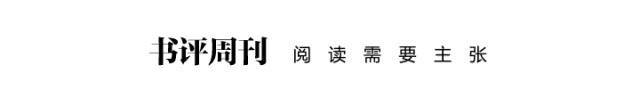 多盈策略
多盈策略
《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是20世纪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对中国早期文明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早期海外中国研究最早在西方风行的权威之作。近日,《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中译本上市,这是原书问世近九十年后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20世纪30年代,顾立雅到访中国,实地考察殷墟等考古遗址和亲手检视众多文物,根据当时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结合中国思想和历史文献撰写了《中国之诞生》,此书是西方第一部利用甲骨文、金文及考古遗址和文物对商周文明进行综合性论述的著作。顾立雅的写作饱含着对中国伟大文明的温情与敬意,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白人种族优越性”,阐述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有特性,对西方中国研究和大众读者认识了解中国产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响。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顾立雅伉俪早期中国研究杰出贡献教授)为顾立雅《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中译本所作的序言,原题为“顾立雅与我”。

作者|夏含夷多盈策略
译者|于歆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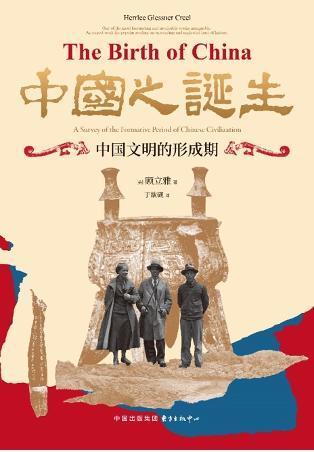
《中国之诞生:中国文明的形成期》
作者:[美]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著
译者:于歆砚 译
版本: 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6月
人们往往有一个误会,即我是顾立雅的学生。这或许情有可原,但实际上当顾立雅教授1974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时,我还在圣母大学攻读本科,刚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直到1984年,我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后,才第一次见到顾立雅。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的复印机旁,时间非常短暂,印象并不太好,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不久后,我受聘为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关于这次聘任也同样有一个误解:大家都以为我接任的是顾立雅的教职,但其实在那些年里,芝加哥大学的远东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for F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现称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有两个传统中国领域的职位:一个是思想史方面的,另一个则是制度史方面的。顾立雅曾经担任的职位是前者,而我受聘的是后者——这一教职之前长期由研究中国唐代的历史学家柯睿格教授(Edward Kracke,1908—1976)担任。
我开始在大学任教后,顾立雅仍会定期来校园用图书馆,并去当时远东系所在教学楼二楼的办公室拜访他的前同事芮效卫教授(David T. Roy,1933—2016)。顾立雅还会经常爬楼梯上到阁楼间我的办公室和我聊天,内容大体是关于1930年代他在北京的日子。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我们的谈话大约隔几个月进行一次,一开始是在我办公室里,后来当他无法再开车时便通过电话进行。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他,是在1989年一场举办于大卫与阿尔弗雷德·斯马特画廊(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现称大卫与阿尔弗雷德·斯马特艺术博物馆(David and Alfred Smart Museum of Art)—的特展开幕式上,展览的主题为“礼仪与崇敬:芝加哥大学所藏中国艺术品”(Ritual and Reverence: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顾立雅将其个人藏品捐赠给了博物馆,包括商代骨甲、商周青铜器及武器,还有一些骨制饰品。所有这些藏品都著录于展览目录,其中大多都是首次刊登。
顾立雅1905年出生于芝加哥。除了在坎布里奇(Cambridge,MA)、北平以及华盛顿特区等地短暂任职外,他的一生都在芝加哥度过。顾立雅整个高中以后的教育都在芝加哥大学完成:1926年,他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并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连续获得了三个不同的研究生学位。第一个学位是1927年他在教会史系获得的文学硕士学位,论文题为《保禄的耶稣复活教义论》(“Paul’s Doctrine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1928年,他的兴趣从基督教教会史转向中国宗教与文化,便在基督教神学与伦理学系攻读神学学士学位,论文题为《〈论衡〉所见之中国卜筮》(“Chinese Divination as Indicated by the Lun Heng”)。1929年,他从比较宗教学系获得博士学位,论文于同年出版,题为《中华主义:中国世界观的演变》。在这篇论文里,顾立雅将他对在硕士论文中研究过的《论衡》的兴趣扩展到了其他许多章节,包括中华主义的起源——此处他指的是后来普遍被称为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oughts)的概念、孔子和儒家、老子和道家(Lao Tse and Taoism,sic)、墨子和民间宗教。尽管对中国宗教很感兴趣,但顾立雅当时几乎不懂中文;在书中的致谢部分,他感谢了一位名叫S. Y. Chan(陈受颐,1899—1978),“如今在岭南大学”的中文导师。他还对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伟大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博士提供的帮助表达了谢意—他从后者那里得以借阅到一些书籍。
驰盈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